作为集成人体组织、细胞样本与临床信息的专业化平台,生物样本库为精准医学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样本和数据支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对疾病认识的不断深化,生物样本库的作用日益凸显,特别是在疾病预防、诊断以及个性化医疗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样本的二次使用往往涉及未来不明或广泛的研究目的,这使得传统的“具体同意”模式在实际操作中面临诸多挑战[1]。基于此,作者认为泛知情同意可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解决方案。
泛知情同意机制的特点在于赋予研究者更大范围的样本使用权限,使其能在获得参与者初始授权后开展后续医学探索。这一机制虽然部分化解了传统知情同意模式的局限性[2],但仍面临诸多挑战。最为突出的问题包括:泛知情同意实施条件的界定标准,以及如何有效维护参与者在未来研究中的隐私保护和知情权[3]。虽然我国已颁布《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等法规对于使用匿名化信息数据和已有的人生物样本提倡减轻伦理审查负担,但在具体操作层面的细则及伦理审查流程仍需进一步完善[4]。
此外,泛知情同意的参与者退出机制的设计与落实构成了这一知情同意模式中不可回避的伦理议题。根据现有研究[5],参与者通常有权撤回泛知情同意,但撤回权的实施条件和限制也需合理设计,以保护生物样本库和参与者双方的利益。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旨在深入探讨生物样本库中泛知情同意的合法化路径、伦理合理性及撤回问题。通过分析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实践以及笔者所在单位的相关经验,为生物样本库管理者、伦理审查委员和相关研究者提供参考,以期共同推动生物样本库伦理与实践的健康发展。
1 泛知情同意的法律框架与争议泛知情同意作为一种特殊的知情同意形式,其法律依据和实践应用面临着诸多挑战。根据《赫尔辛基宣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要求,样本采集、信息数据处理者需明确告知使用目的,并取得权利人的专门许可。与此同时,《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强调样本保藏时必须提供书面知情同意。泛知情同意的核心争议点在于它的“非特定目的”属性,即在样本、信息数据采集、保藏阶段可能只告知将可能用于未来科研目的,而未具体说明研究的具体内容和目的,这与前述法律要求的“特定目的”存在冲突。
在2023年颁布的《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中,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特定情形下可以免除伦理审查(如利用合法获得的公开数据或使用匿名化信息数据开展研究),这引发了广泛争议。笔者认为,该规定体现了减轻科研负担、促进研究开展的积极导向,但对于如何取得匿名化的信息数据以及匿名化实施方式仍然缺乏明确规定,这种模糊性导致实际操作中对泛知情同意的理解和执行标准不一。
泛知情同意常因被误解为降低了知情同意的严格性而受到质疑,实际上,它未能满足知情同意基本原则中的充分告知。然而,由于中国法律对个人信息控制权的重视,以及机构伦理委员会在决策过程中的局限性,泛知情同意可能会被视为缺乏足够法律授权,从而面临合法性质疑[6]。此外,在泛知情同意的具体范围、其与参与者捐献行为的区别以及实施泛知情同意的详细指南等方面尚存在争议和不足。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泛知情同意在实践中的正确实施,也增加了受试者权益保护风险。
2 泛知情同意的伦理要素与实践规范 2.1 基本原则与要素泛知情同意在生物样本库研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要求研究者和参与者之间的沟通必须是充分、透明的,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参与者、研究人员以及任何潜在的商业合作伙伴,都能够理解并同意未来研究的范围、用途和权责。要确保这一知情同意机制的有效运行,应着重关注如下基本原则:
(1) 完全告知:研究者必须全面披露采集、保藏和未来使用样本、信息数据的所有可能用途、保存期限、隐私保护措施及商业利益分配方式,确保信息的完整性与透明度。尤其是在涉及基因、胚胎干细胞等敏感研究时,必须披露潜在的伦理风险,如遗传疾病的潜在风险、不当使用的风险等[7]。
(2) 充分知情:研究者必须如实告知参与者采集、保藏、使用其样本和(或)信息数据的目的,参与者必须能够理解所提供样本及信息数据的含义及潜在影响,包括对特殊或敏感研究类型(如基因研究)的风险认知。
(3) 自主选择:参与者的决定必须基于自由意愿,不受任何强制或不当影响,允许参与者在未来的研究中选择自由退出,而且这种退出行为不会受到惩罚或遭受损失[8]。
生物样本库泛知情同意的实施依赖于四个关键要素:首先是同意范围要素,通过明确研究目的的广度和限制,精确界定可接受的研究类型和范围,为研究活动划定清晰边界; 其次是信息披露要素,要求详细说明样本、信息数据的可能使用方式,全面揭示潜在的研究风险和预期收益,并阐明数据和样本的存储、共享政策,确保参与者获得全面、透明的信息; 第三是撤回机制要素,保障参与者随时撤回同意的权利,并明确规定撤回后数据和样本的处理方式,维护参与者的自主选择权; 最后是隐私保护要素,通过严格的匿名化和去标识化程序,最大程度地保护参与者的个人信息和隐私权益。
2.2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在国际上,《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是欧盟于2018年5月25日正式生效的一部全面且具有约束力的数据保护和隐私管理法规。它旨在对欧盟成员国公民的个人数据提供更高水平的保护,同时赋予数据主体对自身数据的更多控制权。但之后很多研究者提出“动态同意(Dynamic Consent, DC)”模式[9-11],即在GDPR背景下,旨在基于透明和持续选择权实现对数据主体权利的尊重的一种创新管理方式。美国的《通用规则》(Common Rule)是保护人类受试者的联邦政策框架,最早于1991年颁布,并于2018年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规则引入了“广泛知情同意”(Broad Consent)的概念,允许研究人员在生物样本库和健康数据存储研究中获取参与者对未来未指定研究的同意。这种机制旨在平衡研究便利性与参与者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12-14]。这些框架强调了对研究目的持续性同意的必要性,也为泛知情同意的实施提供了灵活性。
为了有效实施泛知情同意,中国的实践需要参考国际经验,同时结合本土法律法规和科研实际需求进行调整和优化[14-15]。例如,一方面需完善样本库的伦理监管机制,强化研究项目的合规性审核; 另一方面应构建全方位样本及信息数据安全防护体系,切实维护参与者的基本权益[16],鼓励创新和技术应用,提高生物样本库的管理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同时保障参与者和研究者的合法权益。
3 撤回权的伦理审视与限制 3.1 法律与伦理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当信息处理建立在个人授权基础上时,权利人可以在任何时候收回其同意。这种权利的设置,不仅体现了个人对自己信息的控制权,也强调了参与者对于自己参与决定的回赎权。2023年8月初,我国出台了《临床试验生物样本伦理管理指南》。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临床试验中涉及生物样本的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等,应获得样本提供者的知情同意。应告知样本提供者有随时撤回同意的权利,并说明撤回同意的方式”。作为全球生物样本库领域的权威机构,国际生物与环境样本库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Biological and Environ- mental Repositories, ISBER)在标准化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国际生物与环境样本库协会最佳实践指南》2018年发布的第四版也提及知情同意撤回问题[17]。
撤回权作为生物样本库研究中提供者的伦理保障机制,其基本伦理价值在于维护参与者的自主决定权和个人尊严。这不仅体现了对个人意愿的尊重,也反映了现代生物医学伦理中的“知情同意”原则:从静态的单次授权,转变为动态的持续性同意过程。撤回权确保了参与者在研究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保持主体地位,能够根据个人意愿、变化的研究情境以及对潜在风险的新认知,自由地退出研究。同时,撤回权也是平衡研究伦理与科学研究需求的重要机制,它在保护个人权益的同时,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道德边界,促使研究者始终保持对参与者权利的尊重和对研究过程的审慎态度。
3.2 实践限制与特殊情况泛知情同意撤回权的实践执行面临多重限制。首先体现为国家利益优先原则下的特殊情形,即涉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如COVID-19研究)或国家安全的研究项目可依法限制撤回权的行使。其次是技术应用层面的不可逆性障碍,典型案例包括干细胞治疗中样本已转化为临床产品,以及匿名化样本因无法溯源而难以执行撤回[18]。值得注意的是,为维护科研连续性,撤回权对已完成研究成果通常不具有溯及效力。特别是在新兴技术背景下,跨境传输审查与人工智能训练用途等场景的出现[19],进一步加剧了监管机制的复杂性,亟需建立更具前瞻性的制度框架。
3.3 撤回权实施中的具体困境分析撤回权作为泛知情同意机制中的核心保障,其实施过程面临诸多实际困境。首先是程序性障碍,表现为撤回途径不畅通、申请流程复杂或响应时间过长,导致参与者难以有效行使撤回权。很多生物样本库尚未建立专门的撤回申请通道和处理机制,部分机构甚至在知情同意书中完全缺失撤回权说明[20]。其次是信息不对称问题,参与者对撤回权的认知严重不足,不了解自己享有撤回的权利,不清楚撤回的适用范围和具体程序,使撤回权形同虚设。
技术层面的障碍同样不容忽视。随着大数据技术和生物信息学的发展,样本数据的分析、共享和再利用日益复杂,多机构合作研究和国际合作项目的增多,使得撤回权的执行面临技术追溯难题。例如,当参与者提出撤回请求时,如何确保已共享至第三方机构的样本和数据也能被有效撤回?如何处理已纳入大型数据集的个体数据?这些问题尚缺乏明确的技术解决方案。
此外,撤回权的执行还面临价值冲突。一方面,过度严格的撤回权保障可能增加生物样本库的运行成本,损害科研效率; 另一方面,过度限制撤回权则可能侵犯参与者权益。特别是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或重大疾病研究中,个体撤回权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更为复杂,需要更为精细的制度设计和伦理判断。
3.4 撤回权的分类与差异化实施策略撤回权并非单一模式,而应根据不同情境采取差异化实施策略。基于实践需求,撤回权可分为三类:完全撤回、部分撤回和有条件撤回。完全撤回是最严格的撤回形式,参与者要求销毁所有生物样本并删除相关数据,终止任何形式的后续研究。这种撤回适用于参与者完全改变决定或对研究产生严重顾虑的情况。在执行完全撤回时,机构应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样本销毁和数据删除,并向参与者提供书面确认。值得注意的是,完全撤回仍存在技术限制,对于已被使用样本、匿名化汇集数据、已发表的研究结果,撤回操作在技术上难以实现。部分撤回允许参与者有选择地限制其样本和数据的使用范围,如仅允许用于非商业研究、禁止基因测序研究或限制国际合作等。这种灵活机制既尊重了参与者的自主选择权,又保留了样本和数据的科研价值。实施部分撤回需建立精细的分类标签系统,对样本使用范围进行明确标识,并在样本库管理系统中设置相应的权限控制,确保符合参与者的意愿。有条件撤回则是在特定条件下允许参与者行使撤回权的折中机制。例如,设置撤回时间窗口(如研究开始后一年内可撤回)、关键节点撤回(如在样本进入特定研究阶段前可撤回)或附加程序要求(如重大项目撤回需经伦理委员会评估)。有条件撤回通过在参与者权益和研究连续性之间寻求平衡,为长期、复杂的研究项目提供了更加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差异化撤回策略的实施需要配套建立分级审核机制。对于完全撤回请求,可采用简化审核流程,注重效率; 对于部分撤回和有条件撤回,则需更详细的审核评估,确保操作的准确性和合规性。同时,应为特殊群体(如未成年人、认知障碍患者)设置代理撤回机制,明确代理人资格认定标准和权限范围,确保弱势群体的权益得到特殊保护。
4 实践挑战与优化路径探索目前,泛知情同意在我国实践中面临多重挑战。首要问题是法律框架的模糊性使其得不到法律支持,且现有法规对泛知情同意的适用范围和效力缺乏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难以把握标准。其次,伦理审查能力参差不齐,部分机构的审查流于形式,难以有效评估研究目的的合理性、必要性及知情同意书的完整性和清晰度。研究表明,生物样本流通环节的知情同意问题(如未说明撤回方式)占临床试验质控问题的4.55%[21]。此外,参与者对撤回权及相关风险的认知不足,也制约了知情权的有效行使。
针对上述挑战,优化路径应从制度完善和实践创新两个维度展开。在制度层面,需要通过立法明确泛知情同意的合法性条件,建立独立且专业的伦理审查机制[22]。在实践层面,应构建便捷的信息平台,加强公众教育,提升参与者权利意识。我院作为获得国家人类遗传资源保藏资质(国科人遗审字[2024]BC0011号)的机构,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解决方案。首先,建立了双轨制知情同意体系:对入样本库管理的研究目的明确的样本采用项目专有知情同意书,对入库储存研究目的不明确的样本采用统一的泛知情同意书,实现了灵活适应与规范管理的统一。
为了平衡管理成本与撤回权保障的关系,我院在现有资源条件下探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通过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将科研管理部门、医务部、伦理委员会、信息科和临床科室有机整合,形成撤回权执行的闭环管理。在操作层面,我院制定了标准化的撤回程序文件,明确了各环节责任人和时限要求,使撤回流程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实现规范化,并在技术方面充分利用现有医院信息系统(HIS),在其基础上开发了样本管理模块,实现了对样本来源、处理状态和使用记录的追踪,为撤回操作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持。这种以制度创新为主、技术辅助为辅的方案,既满足了生物样本库对撤回权管理的需求,又体现了“低成本、高效能”的实践智慧。
基于上述管理框架,在撤回权的具体执行方面,设置了线下书面申请与电话登记的多元化撤回途径,要求提供身份证件和原始同意书编号,并承诺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体现了程序便捷性与安全性的统一。在撤回效力范围上创新性地采用分级管理模式,允许参与者根据个人意愿选择对生物样本和信息数据进行完全撤回或针对特定研究类型(如基因测序、商业转化、国际合作等)进行部分撤回。同时,基于实践需要,明确了两类撤回限制情形:已匿名化处理且无法追溯的样本和(或)数据,以及涉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项目(需经省级卫健委批准)。对撤回后的样本采取差异化处理方案,具体而言:对实体生物样本,根据撤回类型进行处理——完全撤回时予以销毁,部分撤回时则根据参与者指定的限制范围调整使用权限; 并在数据管理上遵循“前向处理”原则,即停止从撤回时间点起的新数据收集,终止对现有数据的更新,已完成的研究和分析结果可以保留,这符合《国际生物与环境样本库协会最佳实践指南》(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Bi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Repositories Best Practices)的规定。为保护特殊群体权益,还设置了参与者丧失行为能力时的代理人制度,体现了人文关怀。针对捐献者离世后撤回权行使问题,采取“机构规范+伦理审查”的简化方案:由生物样本库制定统一的死后样本管理规范,明确规定在捐献者离世情况下,近亲属(配偶、子女或父母)可在特定条件下(如涉及家族遗传风险或样本用途重大变更)向生物样本库提出申请,经伦理委员会评估后决定是否允许调整样本使用范围。
5 结论撤回权作为泛知情同意制度的核心保障机制,对维护参与者的自主决定权和个人尊严具有决定性意义。本研究通过分析撤回权的法律与伦理基础,揭示了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在涉及人体生物样本库的建设与管理中采取的限制性措施,但其对于知情同意撤回权的相关规范仍存在不足,目前在实践中面临的主要挑战为:伦理审查能力有限、信息追溯机制不完善、跟踪审查监管不到位,以及撤回权与科研连续性之间的价值冲突。
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提出了以下规范化路径:首先,建立分级撤回管理机制,将撤回权细分为完全撤回、部分撤回和有条件撤回,采取差异化处理策略; 其次,完善撤回权执行程序,通过建立统一的撤回请求处理流程和信息系统,提高操作效率; 最后,针对特殊情境制定调适方案,包括对捐献者离世后近亲属代理行使撤回权的规范,以及在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的平衡机制。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系统化地构建了撤回权的实施框架,不仅重视法律规范的完善,更注重操作层面的可行性。未来研究方向应聚焦于撤回权的技术实现路径,特别是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中如何实现高效的撤回权管理,为生物样本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坚实的伦理基础。
| [1] |
吴家睿. 生命健康研究伦理治理中值得关注的三种基本关系——对《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的思考. 生命科学, 2023, 35: 557-60. |
| [2] |
陈晓云, 沈一峰, 熊宁宁, 等. 医疗卫生机构泛知情同意实施指南.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20, 33: 1203-9. |
| [3] |
彭华, 袁达, 黄鹂, 等. 泛知情同意概念在我国的引入与实践思考.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2022, 38: 222-4. |
| [4] |
赵励彦, 张玉梅, 刘瑞爽. 生物样本库泛知情同意在中国的实践与思考. 医学与哲学, 2023, 44: 32-5. |
| [5] |
李旭, 王妍, 刘玉秀, 等. 生物样本泛知情同意的撤回权及相关问题探讨. 医学与哲学, 2023, 44: 16-8. |
| [6] |
闻志强, 施梦琪. 个人信息保护视角下知情同意原则的问题审视与完善路径. [C]//《法律研究》集刊2024年第2卷——制度型开放的实现路径研究文集, 2024: 88-104
|
| [7] |
朱玲, 徐新杰, 王焕玲, 等. 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研究的医学伦理审查挑战与困境.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19, 32: 586-90. |
| [8] |
刘锦钰, 赵琼姝, 袁静, 等. 临床研究豁免知情同意的情形分析与探讨.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19, 32: 1243-6. |
| [9] |
Chico V. The impact of 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on health research. Br Med Bull, 2018, 128: 109-18. DOI:10.1093/bmb/ldy038 |
| [10] |
Onstwedder SM, Jansen ME, Cornel MC, et al. Policy guidance for direct-to-consumer genetic testing services: framework development study. J Med Internet Res, 2024, 26. |
| [11] |
Brauneck A, Schmalhorst L, Weiss S, et al. Legal aspects of privacy-enhancing technologies in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and their impact on performance and feasibility. Genome Biol, 2024, 25: 154. DOI:10.1186/s13059-024-03296-6 |
| [12] |
Smilan LE. Broad consent--are we asking enough?. Ethics Hum Res, 2022, 44: 22-31. DOI:10.1002/eahr.500140 |
| [13] |
Lynch HF, Wolf LE, Barnes M. Implementing regulatory broad consent under the revised common rule: clarifying key points and the need for evidence. J Law Med Ethics, 2019, 47: 213-31. DOI:10.1177/1073110519857277 |
| [14] |
Maloy JW, Bass PFR. Understanding broad consent. Ochsner J, 2020, 20: 81-6. DOI:10.31486/toj.19.0088 |
| [15] |
向梦瑶. 试论我国生物样本库知情同意制度[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2024
|
| [16] |
吴翠云, 伍蓉, 曹国英, 等. 基于法规指南探讨生物样本库建库伦理审查要素.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20, 33: 570-4. |
| [17] |
Campbell LD, Astrin JJ, DeSouza Y, et al. The 2018 revision of the ISBER Best Practices: summary of changes and the editorial team's development process. Biopreserv Biobank, 2018, 16: 3-6. DOI:10.1089/bio.2018.0001 |
| [18] |
Corradi A, Bonizzi G, Sajjadi E, et al. The regulatory landscape of biobanks in Europe: from accreditation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Curr Genomics, 2025, 26: 15-23. DOI:10.2174/0113892029313697240729091922 |
| [19] |
冯君妍, 雷瑞鹏. 大数据时代生物样本库发展战略的伦理反思. 科学与社会, 2019, 9: 110-23. |
| [20] |
Hirschberg I, Knüppel H, Strech D. Practice variation across consent templates for biobank research. A survey of German biobanks. Front Genet, 2013, 4: 240. |
| [21] |
赵同香, 蒋向明, 王海英, 等. 探讨药物临床试验生物样本流通环节常见问题及风险前置化管理措施. 中国食品药品监管, 2021(3): 44-51. |
| [22] |
周瑶涵, 胡逸欢, 何蓉, 等. 公共卫生研究的伦理审查要素表构建和审查启示. 中国卫生资源, 2023, 26: 777-85. |
 2025, Vol. 37
2025, Vol.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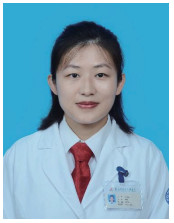 张露远,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医师。苏州市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伦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周围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昆山市医学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2010年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硕士学位,专业为神经病学。2010年7月至2018年8月在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任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2018年8月至今任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伦理办公室主任。长期从事伦理委员会建设及运作、伦理审查和卫生管理等领域研究,具备丰富的伦理管理与医学科研经验。近五年来,在《医学理论与实践》《交通医学》《中国医学伦理学》等学术期刊发表多篇研究论文
张露远,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医师。苏州市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伦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周围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昆山市医学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2010年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硕士学位,专业为神经病学。2010年7月至2018年8月在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任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2018年8月至今任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伦理办公室主任。长期从事伦理委员会建设及运作、伦理审查和卫生管理等领域研究,具备丰富的伦理管理与医学科研经验。近五年来,在《医学理论与实践》《交通医学》《中国医学伦理学》等学术期刊发表多篇研究论文